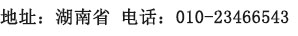上个月,一个四十岁的男人离开旅馆,他体内癌细胞扩散全身,从肺到肾再到头,花了大把钱进去,家里“医不动了”。半年前梁绍芷刚来,这个人就已经住在这里了,跟周围房客打得火热,结束第一次化疗时还想着去海埂大坝转转,“他想,心情好一些,病就能好一些。”可上个月离开时,他得两个人搀着走了。
文
李云帆
1
医院食堂里,他点了一个菜下饭,画有红色方框的左脸颊不那么疼,能吃下更多东西,这得归功于他两周以来的九次放疗。每天从旅馆里醒来的那一刻,他就开始等连一分钟不到的放疗。
吃完晚饭,医院大门,进入农贸市场,顺着仅有一人宽的楼梯走上二楼,独自回到旅馆的号房间。他第二次住这家旅馆,包月订房,每天四十块钱,比按天结算便宜十块钱。他掰指头算,一个月能省下三百元。
中国的癌症发病率持续上升,从年开始已经是主要的致死原因。如今,平均每一分钟就有七人患癌。医院住院部有一千五百多张床位,而实际的病人数量远远超于此。医院附近遍布着大大小小几十家旅馆酒店,有藏在周围小区深处的私人旅馆,也有正规营业的高级宾馆,全用来装病人。
这家旅馆门外并无显眼标识,就医院的牌子,写着“二楼宾馆,干净卫生。”旅馆有二十三间房,房子都朝一个方向,楼下就是市场摊贩在叫卖。医院旁边,每天基本满房。
“来这里住的都是有病的,没病谁会住这里。”梁绍芷坐在办公间里边说边给房客开单,旁边的老式小彩电在播放综艺节目。旅馆除了水泥地面以外,墙体四周是活动板搭建的,夏天房间里闷热,一个男人光膀子搬了把凳子走廊里,玩开心消消乐。
杨立升是云南保山人,患有皮肤癌,目前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淋巴,从六月开始要做33次放疗,脸上的红色方框是定点放疗点。去年,他的小女儿嫁到江苏,大女儿的儿子上小学,他还常跟别人聊起他的江苏姑爷和生意不错的米线铺。
今年,他的左脸颊颧骨处开始隐隐作痛。这样的疼痛起初是可以忍的,他瞒着家人,一如既往在农田里干活,早出晚归照顾他的烤烟。后来疼到无法忍受,医院检查做手术时,他仍以为这不是什么大病,直到年4月11日,医生在对他的左脸颊进行囊肿切除手术的时候发现,这很有可能是恶性肿瘤。
据研究,癌症的死亡率和存活率的在地理方面差异很大,这些差异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更为有限的医疗资源与更低水平的癌症护理,因而农村和欠发达地区被诊断出时就已经是晚期的概率相对更大。
五月,医院开始第一次化疗,一个周期八天,药物花了四多千块。医生在他锁骨右下方置入输液港,化疗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药水滴的很慢也很疼。他大部分时间在发呆,就像现在,他盘腿坐在旅馆床上,抚着一只脚看着门外。在保山做手术时,医生划到他脸部的内神经,现在一碰左脸颊就会流泪,他的左边黑眼珠部分比右边明显大一些。
周末医生不上班,他就等周一。工作日时,医院打来通知他去放射科放疗的电话。总是开着电视玩手机或发呆,“没个人能说说话,太孤单了,就等着晚上家里人干完农活回来打个电话,讲讲治疗讲讲他们在做啥。”在旅馆住了两周,他听不太懂其他地方的方言,跟周围人攀谈也少之又少。这里的病人很多是今天来了,明天就走了。
傍晚楼下的市场开始收摊,门外走廊里人来人往,通向尽头的公共厨房。
2
张子健在厨房里榨猪肉油,妻子李会英拿了两个空的玻璃罐,正好装满,看到插销有空位,她赶紧放下手里的两罐油把自家的电饭煲插上去。
昨天上午三点,李会英把名字在术前文件上签了很多遍,麻醉师要签一份,主刀医生签一份。站在橱柜台子前,正要择下一根坏菜叶扔进垃圾桶时她突然想起医生会诊后跟家属交代的内容,手上动作一滞,眼眶里又盛满泪,医生说如果做手术时病检癌变,且很严重,他的腿就保不住。
年村委会聘他为核桃种植辅导员,他进核桃地处理纠纷,意外被雷电灼伤,当时整个人都昏死过去,医院抢救,过几天脚肿起来了。很多次手术下来,囊肿没取干净。年,患处肿起小包,数次手术下来,医院看医生的白大褂,再把右腿放在手术台上划。
他腿上肿块占了大腿后侧的大半部分,走路会压迫到肿块,直到今年年初,又痛又麻,他拖着腿挪到农田干活。六月四日,医院拍片子,医生看着X光片,形容他大腿内部的囊肿像葡萄一样已经结成一大串。这种情况在当地很少见,很有可能已经转为恶性肿瘤,腾冲的医生建议他们尽快到昆明,昆明的医疗条件相对比较好。
李兰英是李会英的姐姐,她坐在旅馆的床上抽出塑料袋里的X光片和影像检查报告单,片子上左腿是骨头影像,右腿是肿成球的肿块影像。放下片子,她又躺回床上,虽然这是她第一次来看昆明,但除了小旅馆周围,她哪里都没有去。不认识这个陌生地方,也没那个心情。
李兰英帮着妹妹一家换了几家旅馆,最终选了这家。离医院近,每天打扫得挺干净,“住在这里也挺好的,大家都同病相怜”。治病花费对于山区里的农民家庭来说已经很难承担了。跟亲戚家这家借几千,那家借几千,加在一起才凑到了两万多,看病为主,吃的住的能省就省点吧。
整个几天了,张子健在慢慢等周一的手术,手医院,他很少踏出旅馆,为了手术能如期进行,他现在不能发烧感冒。
张子健在背地里偷偷地哭,这些李会英都知道。
3
查风庆也在等着。她站在走廊的窗边,带着布帽子,头发灰白,手腕上系着住院部的绿带子,上面写着她的编号和胸外一科,已经编了号码,医院。
昨晚她的女儿查林燕挨个打给亲戚借钱,“能凑到就治,凑不到……就没办法。”接着她打电话给工地上代班的女工,七天前在工地上,她被机器误伤,缝合的针脚还留在她的手背上,可眼下顾不上这件事。就在上周,她带着母亲从家里的村子到六盘水,再坐十个小时的火车到昆明。大病医保跨省报销额度不高,但她不管了,治病最要紧。
查林燕从没来过昆明,她哪里都不敢去,最远到马路对面买点生活用品,站在路牌面前,她一个字都不认识,生怕多走几步就会走丢。
研究表明,中国最普遍的4个癌症是肺癌、胃癌、肝癌、食道癌。这几种癌症超过了中国癌症诊断的半数,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有更高的发病率。
另外,许多癌症早期表现比较隐匿,像肺癌:早期不一定有症状,或者出现咳嗽、咳痰、胸闷等症状,与感冒、气管炎之间没有什么差别;肝癌、胃癌的早期表现可能仅有上腹部不适、饱胀的感觉等表现。这些表现实在太普通了,无法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大多数患者一旦确诊就属于晚期。
年3月,查凤庆确诊为肺癌,连着十几天晚上她都睁眼到天亮,平躺床上呼吸不顺畅,翻个身,继续发愁,怕凑不到钱治病,怕年龄大下不了手术台,熬到清晨,去医院挂盐水又靠在椅子上打瞌睡,吊了一个多月盐水,止住病情。四十年前她只有二十多岁,得了肺结核,当时没有根治,不听儿女的劝,依然干很多很重的农活,咳嗽加重,呼吸不畅,有一天感冒到喘不过气,要靠吸氧支撑。
查林燕也睡不着。她怕治不好,更怕人财两空。她不敢跟查凤庆提起,只要一说,查凤庆的泪就止不住。但刻意隐瞒其实没用,夜里两人睡在一张拼起来的床上,女儿心里在想什么,查风庆一清二楚。
今天的午饭,母女俩靠清水煮白菜解决了。现在查林燕手头只有几百块的饭钱,“买便宜的,还能多吃一点,吃得好了就吃不饱了。”早上,她们两去楼下的菜市场买菜,逛了两圈,路过鲜肉类区,只能快步走过,价格都不敢问。“问了不买,人家还不骂你。”
4
房间里的人,睡的睡,发呆的发呆。房间外的走廊上,抱着一堆白色床单的梁绍芷来回走着,有时往一些房间里望一眼,也不进去,立马转头又走了。
梁绍芷头发染成棕红色,涂了层薄口红,在厨房旁别的的天台上洗床单,两台洗衣机在运作。四年前来旅馆打工,后来回家带孙子。她家住附近,年龄大不好找工作,在家也没事,半年前来了旅馆打工,值班时开房、退房、打扫都归她管。打扫房间时,她一直带着口罩,有时看到房客肤色蜡黄瘫在床上,她会习惯性的用力扯一下口罩,试图把整张脸遮住。
上个月,一个四十岁的男人离开旅馆,他体内癌细胞扩散全身,从肺到肾再到头,花了大把钱进去,家里“医不动了”。半年前梁绍芷刚来,他就已经住在这里了,跟周围房客打得火热,结束第一次化疗时还想着去海埂大坝转转,“他想,心情好一些,病就能好一些。”可上个月离开时,他得两个人搀着走了。
旅馆楼下,农贸市场的店铺门面中有售卖精心包装好的鲜花水果,也有丧礼用品的商店,黑底白字的“奠”招牌就竖在墙上。
“有些病重可以医,但家里没钱,住里面的人都想活下去,万一能医好呢,可医好的又特别少,都是怕人财两空。”她印象里大部分人都是越治越糟糕,她常冒出不想继续干的念头,她害怕以后像他们一样蜷缩在小房间里,头发大把掉,被病痛折磨的生不如死。
年大概超过三成的癌症患者能够存活5年以上,女性的存活率将近半数,而男性仅有四分之一,存活率最低的确是西南地区。
梁绍芷看过得了胃癌的房客,吃完饭会立马全部吐出来;也充当过和事佬的角色,劝解那些家里不愿再掏钱治病的病人亲戚,不让他们在旅馆房间吵架;她还进过那些没力气也没心情收拾自己的病患的房间打扫,臭气熏天。
眼下,她翻着入住登记单,上面有的来个几天就走了,有的不停的来,不停的治。她发现,以前入住登记的六十多岁居多,现在四十多岁也挺多的。
5
童来仙属于这里病症比较轻的病人。二十天前,她拿着单子穿梭于各个科室检查,手心直冒冷汗。一项项检查到第四天晚上,她躺在旅馆床上,打电话给她姐姐,害怕的在电话里大哭。周围的人基本都是癌症患者,生怕检查出自己也有什么病,深夜她的精神高度集中,关掉所有的亮光,还是睡不着。好在检查结果是乳腺上有囊肿,排了半个月的队,结果只用做个十分钟就能结束的微创手术。
她的胸部眼下还在用绷带缠着,像她这种小手术患者,医院从没让她踏进过住院部的病房。打完电话的第二天她姐姐就来了。她们住在旅馆里已经将近一个月,饭碗摆在房间的桌子上,里面还有中午没吃完的饭菜。虚惊一场,她闲的没事就去串门,跟周围的邻居聊天,打听他们情况。
她像清楚这里所有的事情。一个小时前她遇到一个16岁小姑娘,要去做消炎。人走后,她便跟人说,这小姑娘太可怜了,一边胸部是乳腺囊肿,那次做微创手术,她还安慰她父亲别哭。另一边无法确定是否是恶性肿瘤,做的是穿刺活检,尽管打了局麻,还是疼得直不起腰,女孩和家人都在哭。床位有限,她没能住院观察,隔天,穿刺的创口化脓了,她奶医院消炎。
张静(化名)从童来仙身边走过,她俩靠在窗边聊了几句。张静刚走一会儿,童来仙就凑过来,挤着眉朝着张静离开的方向怒了怒嘴,她说这是张静第三次跟丈夫住进旅馆,她的第三次化疗就要开始了。童来仙说张静每天带着红格帽子是因为她的头发都掉的差不多了,她得的宫颈癌太严重了,没法直接动手术,每天疼得走路像踩在棉花上,多说一句话的力气都没有。张静房间的垃圾桶里堆满了她丈夫抽完的烟蒂。
童来仙止不住地说,说前几天住在隔壁的老公公在做穿刺时休克了,家人把他转到北京医院;说她有个老乡得了甲状腺淋巴结,医院做手术没有根治,后来又复发了,还得来这里。说着说着,觉得自己身上的病都不是事儿。
童来仙另一头的邻居是查凤庆,昨天,童来仙看到查凤庆家的六个儿女都来到了旅馆,医院做手术了,童来仙说她的病情不轻,手术持续时间会非常久。
6
旅馆走廊的另一边尽头蒋先凤来旅馆两天了,她刚做完的核磁共振要求空腹,下午六点是她的早饭时间,一大碗小米辣她吃了将近三分之一,不吃辣子饭就没味道,辣的不停的“呲呲”的吸气,最后喝了一杯茶水才压下去。
蒋先凤这次是来复查的,离她年查出乳腺癌过了六年,期间化疗二十次,乳腺癌复发、癌细胞转移到肝上肺上,六年抗战在这次检查指标正常中告一段落。抗癌是一场持久战。她每次端着保温杯走过走廊,看到房间里的其他房客,她想,每天咿咿呀呀叫唤的人,哪能战胜病魔。
蒋先凤一说起年的三次化疗经历她就想笑。丈夫忙着赚钱,孩子又在外地打工,三次化疗,她没让任何人陪她。但化疗很危险,医院要求必须家属陪同,蒋先凤就让在旅馆上班的女同事都当她的家属去签字,有一次还她跟医生说“我家属出去了。”自己把名字给签了上去。
每一次化疗结束,她都是坐车回昭通,只休整几个小时后,就自己去民政局医保中心报账。等下一次化疗,她又一个人从昭通坐车过来复查,“我又不是七老八十走不动。”但是,她每次化疗完都不停呕吐,水都喝不下,毛发掉到连睫毛都在劫难逃,她背在背后的右手臂上有化疗时置入PICC管留下的疤。
旅馆的电视里播放着治疗肝硬化的医药广告,房间里没开灯,电视屏幕光印的白墙发亮。刚刚小女儿给她发了一条北京治白癜风哪家好早期白癜风要怎么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