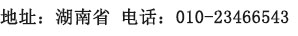本文内容已经过同行评议,以优先出版方式在线发表,可作为有效引用数据。由于优先发表的内容尚未完成规范的编校流程,《中华外科杂志》不保证其数据与印刷版内容的一致性。
周艳召,朱瑞利,欧阳敬中,等.超声引导下经皮射频治疗心包下肝脏恶性肿瘤的临床疗效[J].中华外科杂志,,58(10):-.
超声引导下经皮射频治疗心包下肝脏恶性肿瘤的临床疗效周艳召 朱瑞利 欧阳敬中 喻克丽 王征征 李庆军 周进学
{医院肝胆胰腺外科}
射频消融术是根治性治疗肝脏肿瘤的手段之一[1,2]。近年来,因其创伤小、并发症少、恢复快、可重复使用的特点,在临床上迅速得到应用。有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最大径≤3cm的肝癌,射频消融术后的1、3、5年总体生存期、疾病控制率与手术切除相似[3,4]。但对于靠近特殊部位(如膈肌、胃肠道、胆囊、肝包膜、下腔静脉等)的肝脏肿瘤,因为安全消融距离不足,会增加不完全消融的风险和引起"热损伤",进而影响肿瘤局部进展率,引起严重并发症。有报道证实,邻近膈肌[5,6]、胃肠道[7]、肝包膜[8]的肝脏恶性肿瘤的射频消融效果并不会受到影响,但对心包下的肝脏恶性肿瘤的射频消融效果研究较少。我们回顾性分析了26例心包下肝脏恶性肿瘤的消融效果和并发症发生情况,探讨其临床效果和安全性。
资料与方法一、一般资料
回顾性收集年1月至年11月于我院接受超声引导下经皮射频消融治疗的肝脏恶性肿瘤的患者资料。纳入标准:(1)肝恶性肿瘤在矢状位或冠状位成像中距离心包≤1cm;(2)单一结节肝脏恶性肿瘤5cm;(3)存在多结节肝脏恶性肿瘤(≤3个,单个最大径3cm);(4)无血管侵犯和肝外转移;(5)Child-Pugh分级A级或B级;(6)经穿刺活检或经两种影像学检查结合临床情况确诊为肝脏恶性肿瘤,并在我院行超声引导下行经皮射频消融。排除标准:(1)严重心、脑、肺、肾等器质性病变不能耐受射频消融术;(2)血小板计数50×/L或凝血酶原活性50%;(3)行姑息性减瘤消融术。
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本研究共纳入26例患者31个肝脏恶性肿瘤。男性21例,女性5例;年龄55岁(范围:40~77岁)。原发性肝癌14例,转移性肝癌12例。肿瘤最大径(2.3±1.0)cm(范围:1.0~4.2cm)。通过肿瘤最大径进行1∶1匹配同期收治的27例非心包下患者共36个肝脏恶性肿瘤。两组患者基线特征见表1。
表1 两组肝脏恶性肿瘤患者临床特征的比较
本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号:CT),患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二、仪器与方法
选用三星ACCUVIXA30彩色超声诊断仪,腹部探头频率为3.5MHz,探测深度为20cm。射频消融仪器选用韩国STARmed公司生产的冷循环射频消融系统,由射频发生器、冷循环水泵、负极板及附件组成。最大输出功率为W,温度控制范围为15~℃,消融电极针采用冷循环单电极消融针,根据肿瘤最大径动态调整前端裸露电极长度(0~4cm),根据电极前端裸露长度调整输出功率及消融时间。
三、消融过程
所有患者行术前评估并制定消融计划,患者在清醒状态下接受镇痛、镇静(射频消融治疗前20min使用氟比洛芬酯注射液50mg、地佐辛注射液5mg静脉注射)和局部麻醉。超声引导下射频消融治疗由具有5年以上射频消融经验的肝胆外科医师施行,超声引导由经过培训的超声科医师按计划在超声引导下经皮避开重要结构和器官,对于体积较大(最大径≥3cm)或靠近重要管道(最大径≥3mm的动脉)的肝脏肿瘤,可提前并排布置多个单头电极(双电极之间最大距离≤2cm)或通过联合入路进行消融,避免使用多头电极针及术中大幅度调整电极针。消融使用自动挡,每次消融时间为8~12min,消融过程中即时采用超声评估消融效果及即时并发症。必要时进行多次重叠消融以获得足够的消融区域。除肿瘤位于肝脏包膜下外,所有肿瘤的消融边缘均应在肿瘤边界外至少0.5cm处。当射频消融产生的回声区覆盖整个肿瘤且在超声上获得足够的消融边缘时(图1),消融过程结束,在重新定位和拔出电极针时,进行针道消融以降低出血和肿瘤播散的风险。
图1 肝脏2段原发性肝癌患者(男性,52岁,肿瘤最大径约2cm)影像学检查图像:A示术前增强MRI动脉期图像,可见肿瘤明显强化(箭头所示);B示术前增强MRI静脉期冠状位图像,可见肿瘤强化程度降低(箭头所示);C示超声定位图像,箭头所示为肿瘤;D示左侧入路单针布针穿刺入肿瘤后超声图像(箭头示射频电极针尖);E示患者消融术后1个月复查增强MRI图像,消融区未见强化(箭头所示),消融区域完全覆盖原病灶,考虑消融完全;F示术后增强MRI冠状位图像,消融区未见强化(箭头所示)
四、疗效评估及随访
本研究遵循了肿瘤消融国际工作组提出的图像引导下肿瘤消融术语和报告标准的标准化建议[9],评估射频消融治疗心包下肝脏恶性肿瘤的一次性完全消融率、主要技术有效率及并发症情况。所有患者在射频消融后第1天接受多期增强CT或MRI检查,并进行实验室检查和肿瘤标志物测量,评估肿瘤消融情况和并发症。
患者出院后的第1个月和前2年每3个月进行多期增强CT或MRI检查(图1),之后每4~6个月进行复查[10]。在射频消融治疗1d后获得的增强CT或MRI图像上,如果消融部位或者消融边缘存在活性肿瘤定义为不完全消融。主要技术有效率定义为接受射频消融治疗1月后在被完全消融的肿瘤中成功根除目标肿瘤的百分比。肿瘤局部进展(localtumorprogression,LTP)定义为已完全消融的肿瘤在后续随访过程中的再次出现[9]。可疑复发病灶必要时穿刺活检确诊。
五、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差异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差异的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将所有风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再将单因素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风险因素或可能影响结果的风险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术后第1天行增强MRI或CT检查评估消融情况,心包下组射频消融术后肿瘤一次性完全消融率为80.8%(21/26),非心包下组为92.6%(25/2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心包下组5例和非心包下组2例未完全消融,按照消融计划均接受了补充射频消融,再行增强MRI评估均达到完全消融(图1)。两组患者术后1个月时未见LTP的证据,主要技术有效率为%。患者手术前后影像学资料见图1。
一、术中并发症发生情况
两组患者未发生导致射频消融中止的严重并发症(如心脏骤停、死亡、大血管出血等),术中监测两组患者的心血管状态和血流动力学。心包下组消融术中出现心动过缓1例、低血压1例和高血压2例,患者无心律失常或缺血性心脏病症状;非心包下组术中发生高血压2例,心动过速1例。所有患者的心脏症状和血流动力学改变均在短暂的消融暂停后恢复正常,消融术后不需要药物进一步治疗。
二、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心包下组消融后发热2例(7%,2/26),非心包下组发热4例(14.9%,4/27),给予对症处理后均好转。心包下组出现1例肝脓肿、1例术后腹腔出血,分别给予抗菌药物治疗、给予止血药物留夜观察后好转。非心包下组出现1例术后腹腔出血,给予止血药物留夜观察后好转。两组患者均未出现与消融相关死亡事件或肿瘤沿针道播种等严重并发症。
三、不完全消融的影响因素(表2、表3)
表2 心包下肝脏恶性肿瘤不完全消融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表3 心包下肝脏恶性肿瘤不完全消融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边缘至心包距离≤5mm是影响射频消融效果的可能危险因素,我们将临床中可能的影响因素(肿瘤位置、有无腹部手术史、肿瘤最大径)一并纳入多因素分析,发现仅肿瘤边缘至心包距离≤5mm是影响射频消融效果的独立危险因素(P=0.)。位于Ⅱ段、Ⅲ段、Ⅳ段、Ⅷ段肿瘤的一次性完全消融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肿瘤最大径≥3cm与3cm、消融过程是否应用人工腹水,其一次性完全消融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讨论肝脏恶性肿瘤进行射频消融时常因消融安全距离不足和"热损伤"导致较高的肿瘤残留率和严重并发症[11,12],从而限制了射频消融的适用范围。心包下肝恶性肿瘤由于解剖位置特殊,实施射频消融时操作困难,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与非心包下肝恶性肿瘤消融方式相比,心包下肝恶性肿瘤消融时术者多采取保守的消融策略,以避免射频电极针直接穿透心包或间接造成心肌的热损伤,这将导致消融肿瘤边缘和消融时间不足。(2)本质上,与邻近下腔静脉或肝内大血管附近肿瘤的消融方法差异不大,心脏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散热器",可能由于心脏分散了热量,从而导致肿瘤的不完全消融。
近年来,已有心包下肝脏肿瘤消融治疗的相关报道,Schullian等[13]倾向性匹配研究结果显示,利用立体定向射频消融术对79例患者共个心包下肝癌进行了消融,其一次性完全消融率为95.6%,主要技术有效率为99.1%。Kwan等[14]纳入33例接受射频消融的患者资料,根据肿瘤边缘至心包的距离是否≤1cm分为两个亚组,邻近心包(距离≤1cm)和非邻近心包(距离1cm)肿瘤的一次性完全消融率分别为86.7%和83.3%(P=1.00),两组肿瘤复发率分别为20.0%和22.2%(P=0.95),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6.7%和11.1%(P=1.00)。Carberry等[15]的研究结果显示,与肝切除术组相比,在心脏附近进行经皮肝癌微波消融术的LTP发生率相似,且不会增加心脏并发症。本研究共纳入接受射频消融的26例心包下肝癌患者和27例非心包下肝癌患者,也证实了与非心包下组相比,射频消融治疗心包下肝癌安全有效,两组一次性完全消融率和主要技术有效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围手术期并发症风险无明显增加。但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肿瘤边缘至心包距离≤5mm是影响射频消融效果的独立危险因素。
心包下肝恶性肿瘤的射频消融存在安全消融距离不足和潜在的医源性心脏机械损伤的问题。既往有关于射频消融治疗肝癌术后发生出血性心脏压塞导致患者死亡的报道[16],为了改善消融效果和避免发生类似严重并发症,我们对心包下组部分(50.0%,13/26)患者实施了人工腹水技术。滴注人工腹水[17]被认为可以减轻消融治疗包膜下肝肿瘤时的疼痛程度及改善肝顶部肿瘤的超声显示效果。但我们在进行心包下组亚组分析时发现,两组在一次性完全消融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能与本研究病例数纳入不足有关,尚需要进一步研究人工腹水在心包下肝癌射频消融中的有效性。关于治疗效果,虽然本研究中心包下组的一次性完全消融率略低于非心包下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两组在随访期间的主要技术有效率相似,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对于多次腹部手术导致器官粘连严重或人工腹水建立失败且合并肝硬化的患者,可选择腹腔镜辅助射频消融治疗[18]。一般而言,保守性消融策略是首选方案,以避免直接穿透心包和附带的热损伤等并发症发生,但这可能会因消融时间或消融范围有限而导致不完全消融。然而就治疗效果而言,尽管在本研究中,心包下组的技术成功率略低于非心包下组,但两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两组主要技术有效率相似,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基于这些结果,不应因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