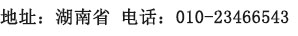二.生存者——对生存的担忧
当癌症侵袭患者身体的同时,也侵袭了他们的心理,威胁到了一个人的自我和未来。未来越是充满不确定感,越显得有价值。癌症激发了“对生存的终极担忧”,Yalom将这些担忧描述为隔离、意义、自由和死亡。这些最基础的担忧让癌症患者内心充满恐惧的同时也提供给他们一个机会。如何帮助癌症患者重建当前的生活,丰富未来的意义,是一件很重要的任务。
患癌症是一种让人感到隔离的体验。当得知癌症诊断时,无论是患者还是他们的照顾者都被吓坏了。在这个曾经健康的人和他周围人之间突然出现了一条裂隙。患者被迫面对他们自己的生存焦虑。这个裂隙很难弥合。这时患者非常需要与他人建立联系,但他们感知联系的能力却极大地减退了。患者常常感到没人能理解他正在经历的事情,也可能会感到有必要保护他的家人远离自己的痛苦。同样,他们的亲人此时感到很难与他们分享自己的感受,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觉得自己此刻的需要是不重要的。这种彼此沟通的缺乏更放大了他们的隔离感,这种隔离感继而又加深了他们的死亡焦虑,因此他们理解“不存在”的意义的方法之一就是让自己孤独。社会隔离成了他们即将经历死亡的预兆。Yalom将隔离的生存冲突的描述为“我们完全隔离的意识与我们希望与他人保持联系,受到保护,获得归属感之间的冲突”。对癌症患者来说,与其他癌症患者在一起可能会是一剂对抗隔离感的特效药。
癌症缩短了患者的未来,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常常会引起他们对生命意义的拷问。就像Yalom所说“我们是否一定会死亡,我们能否够构建自己的世界,是否每个人最终都会孤独地存在于一个冷漠的宇宙中,那么生命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很残酷,却无法避免。它的表述可以有多种形式。对于癌症患者来说,这个问题可能是“为什么是我得癌症?为什么是现在得癌症?”也有患者可能会问“我过去做了什么让我得癌症?”或者“关于自我、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以及我所在乎的事情,癌症教会了我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在努力地寻找癌症对我们生命的意义。
生存问题是关于如何在毫无根据可循的情况下管理现实生活。患者面临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必须选择如何生活,是我们“创造”自己的生活。癌症迫使患者对他们的自我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重新定义和规划。癌症影响体像和对自我的感觉,患者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驾驭这些改变。患者必须做出选择,他们允许癌症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方式。他们是否要选择“把它抛在脑后”继续生活,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还是要有意识地对自己的生活做出一些改变?如何重新回归社会?这些都是生存者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而生存者内心的不确定感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往往成为癌症生存者焦虑的原因,导致他们现实生活质量的下降。
毫无疑问,最深层的存在问题是面对死亡。对很多人来说,这可能是第一次直面自己的死亡。对他们来说,死亡曾经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至少是他们能控制的一种想法。但现在“它就在你面前”,有些患者将死亡描述为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她得头顶。对死亡的恐惧被激活,无论她是早期患者还是生命只剩几周或几个月的晚期患者。
情感表达
不幸的是,在大众中有一个普遍的信念,那就是保持“积极的态度”非常重要。如果你得了癌症,无论如何,你都要避免、抑制甚至否认“负性”情绪。然而,癌症不可避免地召唤着阴郁的情绪——恐惧、愤怒、悲伤。很多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属被囚禁在“积极思考的监狱中”,觉得向这些情绪屈服就等于向癌症屈服。关于癌症的负性感觉是无法避免的,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它对自己的亲人造成的影响感到害怕、愤怒、痛苦和悲伤都是很自然的。是否要要表达,怎样表达,何时表达常常是癌症患者所面临的挑战。一部分患者对是否要表达负性情绪积极地做着心理斗争,而另一部分患者则压抑了自己的负性情绪。
有研究表明,口头叙述艰难的情感经历能够提高生活满意度。Pennebake的关于表达性写作的专著阐述了将艰难的情感经历写出来将大大有益于身心健康。我们认为口头交流癌症带来的情感挑战也会获得相似的益处,并提高情绪的自我效能感。
对癌症的评估必须包含诊断、分期、预后、目前的治疗和治疗常见的副反应。医生需要这样的全方位视角,来面对患者对疾病及其严重性的意识并作出反应。患者自己的主观构想跟临床医生所认为的事实往往有很大差别。心理医生应当尽力与患者的主治医师、肿瘤科专科医师等获得联系,理解导致患者现况的现病史和既往史。若对患者医疗背景的了解不足,心理医生很难为他们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
三.常见及晚期精神症状处理
失眠和抑郁、焦虑是癌症以及抗癌治疗中常见的并发症。据估计有大约1/3的癌症患者会经历心理社会痛苦。心理社会痛苦包括精神障碍,同时也包括未满足完整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的情绪状态。抑郁、焦虑障碍和适应障碍是癌症患者最常见的精神障碍类型。另外,谵妄可能在住院和晚期癌症患者中更高发,几乎达到25%。
1.失眠
1)概述
失眠通常指患者对睡眠时间和/或质量不满足并影响白天社会功能的一种主观体验。临床常见的失眠形式有:1、明显的入睡困难,睡眠潜伏期延长(超过30分钟);2、睡眠维持困难,觉醒次数和觉醒持续时间增加(大于2次);3、睡眠质量下降,睡眠浅、多梦;4、总睡眠时间缩短,通常少于6小时;5、早醒和日间瞌睡增多等。
处理原则:对癌症患者睡眠障碍的治疗首先是针对原发病的治疗,遵守癌症治疗原则。在抗癌治疗的同时,应对睡眠障碍给予必要的处理,针对不同的病因采取不同的措施,以达到缓解症状、保持正常睡眠结构、恢复社会功能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治疗目标。对急性失眠患者应早期药物治疗;对亚急性失眠可以早期药物治疗联合认知行为治疗;对慢性失眠患者建议咨询神经精神科专业医师。
2)药物治疗
国际睡眠障碍专家研讨会提出“按需治疗”和“小剂量间断”使用催眠药物的原则,即根据患者白天的工作情况和夜间的睡眠需求考虑使用短半衰期镇静催眠药物,强调镇静催眠药物在症状出现的晚上使用,症状稳定后不推荐每天晚上用(间歇性或非连续)。治疗失眠应选择非苯二氮?类药物作为一线药物。药物治疗的前几周一般采用持续治疗,在随访过程中根据患者睡眠改善状况适时采用间歇治疗。当患者感觉能够自我控制睡眠时,可考虑逐渐停药。停药要缓慢,需要数周至数月时间,常用的减量方法为逐步减少夜间用药量,在持续治疗停止后,可按需间歇用药一段时间,禁止突然停药。
(1)非苯二氮?类药物:主要包括唑吡坦、佐匹克隆、扎来普隆等药物,选择性拮抗GABA-BZDA(r-氨基丁酸-苯二氮?)符合受体,仅有催眠而无镇静、肌肉松弛和抗惊厥作用。
(2)苯二氮?类药物:非选择性拮抗GABA-BZDA复合受体,具有镇静、肌肉松弛和抗惊厥的作用;通过改变睡眠结构延长总体睡眠时间,缩短睡眠潜伏期。一般根据患者失眠的不同情况选用不同的药物。入睡困难者服用见效快、作用时间短的短效药物以避免晨醒后药物的持续效应,如三唑仑、咪达唑仑等。睡眠不深又早醒者可服用起效缓慢、作用时间持久的长效药物,如艾司唑仑、氟西泮等。
(3)抗抑郁药:对伴有抑郁情绪或疼痛的睡眠障碍患者,抗癌治疗同时应使用有助于镇静催眠的抗抑郁药,如米氮平、曲唑酮、阿米替林等。米氮平能缓解抑郁患者的睡眠障碍症状。曲唑酮抗抑郁作用比较弱,但催眠作用比较强,可以治疗睡眠障碍,也可以用于治疗催眠药物停药后的失眠反弹。
(4)抗精神病药物: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如奥氮平、喹硫平等也逐渐用于睡眠障碍患者。对于癌症患者,特别是使用化疗药物或阿片药物所致恶心、呕吐及食欲下降的患者,使用小剂量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不仅有助于改善患者睡眠,还可减轻患者的恶心、呕吐,改善食欲。使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改善睡眠应注意小剂量治疗,喹硫平12.5mg/晚,最高剂量50mg/晚;奥氮平2.5-5mg/晚。
赞赏